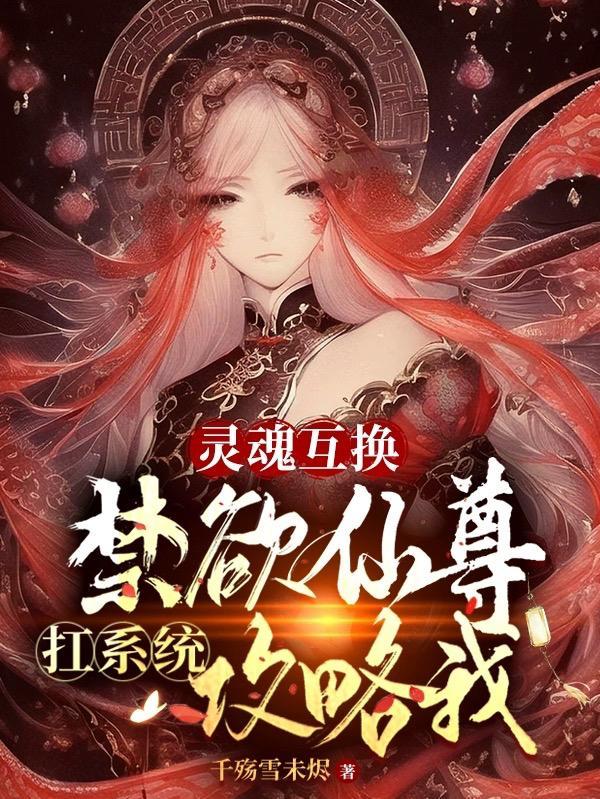乐文小说中文>桃花妆免费阅读全文 > 第133章 公主 呸道貌岸然的伪君子(第1页)
第133章 公主 呸道貌岸然的伪君子(第1页)
一个时辰后,面无表情的秦寿坐到了雒妃面前。
不知是不是身上有伤的缘故,雒妃老觉得他面色较之平常更为苍白了一些,但他精神尚好,半点都看不出来是受过伤的。
雒妃背靠软枕,黑白分明的桃花眼微微垂着,本就白的脸上多了几分虚弱无力的病态美。
她旁的也没问,就直接道,“那僧人是谁?”
秦寿淡淡地瞥了她一眼,“当下普陀寺的主持乃玄明法师,玄明法师乃得道高僧,擅观相术,诸多高门权贵抱着银子来,也不见得能得到玄明法师半句指点。”
雒妃也没打算他,安静听着。
“这玄明法师早年曾有一生死劫难,后来遇上贵人,劫难化解,贵人却是替他挡了劫难殒命,当时这贵人还留下了个尚在襁褓的婴孩,玄明法师心善,秉着报恩的心思,将这孩子带回了普陀寺,并亲自教养,只等他长到自立,就放出山门,毕竟这孩子根本不是佛门中人不是。”
秦寿拢着手,凤眼低垂,从他脸上看不出半分的异色,“后来这孩子长到十岁,却展现出非凡的慧根,并与玄明法师说,要遁入空门,潜心修行,玄明法师起先并不同意,但这孩子却自行剃去头发,玄明法师如此才收了他做关门弟子。”
“这孩子如今法号得舍,如今已有二十五六的年纪,在普陀寺,所有人都将他看做是下一任的主持。”秦寿说完最后一句话,他抬起眼,瞧着雒妃。
雒妃微愣,得舍的名号她从前就听说过,且这人,日后也会投奔秦寿麾下,在她要死的那会,还有人提议,要将得舍奉为国师。
所以——
“你也是来找得舍的?”雒妃神色一冷,眸底酝酿出凛冽的戒备来。
秦寿就晓得她是这样的反应,他不自觉隔着衣衫摸了摸肚腹的伤口,摇头道,“是也不是。”
雒妃冷哼,她就晓得这人要跟着来普陀寺没安好心,“是就是,不是就不是,本宫不晓得驸马何时这样婆婆妈妈。”
秦寿撩了下袍摆,左腿叠架到到右腿上,越发显得他人高腿长,“本王是来找人的,可不是来找得舍的。”
雒妃明显一脸不信。
秦寿见她粉唇干涸,顺手端了盏温水给她,竟然耐着性子解释道,“不管公主信或不信,得舍他日后自会来找本王,是以,本王这会还不稀罕他,本宫想找的人,可是得舍的师父,玄明法师。”
他这样说,雒妃反而更戒备了,一个得舍日后就能让秦寿的谋逆造反宣扬的理所当然,若是玄明,她不敢去多想,却是打定注意不让他得逞。
秦寿哪里还不晓得雒妃的心思,他微微一笑,“公主莫要担心,本王说过,只要公主乖顺一些,一切都好商量。”
他顿了顿,又道,“且本王找玄明,也不是要他出山,他一得到高僧,早是六根清净的方外之人,本王还于心不忍他再沾染红尘,只是旁的事罢了。”
“何事?”雒妃紧接着问道。
但这话一出口,她瞧着秦寿看过来的兴味目光,心头就已经后悔嘴巴太快。
秦寿也没逗她,沉吟片刻才道,“这也是可以告诉公主的。”
“本宫不想知道!”雒妃素手拍了下锦被,瞪大了眸子,本想有气势一些,可她还在病中,眉目娇弱,又哪里有半分的威慑力。
秦寿定定望着她,忽的靠的近了些,低声道,“玄明法师擅观相之术,本王请他为我等两人看看。”
雒妃怔忡,忽的她怒道,“胡说八道!”
秦寿却是已经坐直了,仿佛没说过刚才那话一般。
雒妃舔了舔发干的唇珠,视线在他腰腹间转了圈,又问道,“昨日行刺的歹人可有线索了?”
秦寿施施然,手搁膝盖上轻敲,“不是皇后,但总与她背后的司马家脱不了干系,亦或是京城三王也是说不定,不然可不就单单只是掳公主入山林,而是当场就取了公主性命去。”
这点,雒妃也是晓得的,既然是行刺,那来的歹人多半都是死士,拷问不出什么,故而一时半会也是没头绪,不若眼前皇后的事要紧。
她捏着锦被角,拧着平眉,“既然要在普陀寺住上几日,不抓住皇后的马脚太过可惜。”
秦寿点头,他起身,弹了弹袖子,“晓得了,既然是公主想的,那便如公主所愿。”
雒妃眉梢一挑,她可没想到他会帮她。
秦寿居高临下地看了她一眼,旋身欲离去,“公主好生养着。”
雒妃也不留他,更不想过问他那伤如何了,总是她刺他一刀,他还活得好好的,哪里像她,被刺一剑,就没了活路,是以,还是她吃亏的多。
自昨晚的行刺,雒妃身边除了盯着皇后的鸣蜩不在,就是息芙吃住都与雒妃一起,硬是在赶她,她也是不去隔壁的厢房休息。
顾侍卫心里也很是愧疚,于是便同季夏越发尽心尽力地护卫雒妃安危,每日吃食,都是季夏亲自动手做的,半点不假他人之手。
下午晚些的时候,皇后司马初雪过来了趟,她瞧着雒妃气色渐好,便与雒妃闲聊几句就作罢。
是夜,雒妃已经安置了,她用了药,舌根发苦,吃了好几个甜嘴的果脯,也没见好,便精神恹恹的早些休息。
哪知亥时中,她蓦地惊醒过来,就见床榻前站着道人影,她呼吸一窒,刚想大喝一声,那道人影迅疾弯腰,捂了她的嘴。
借着氤氲暮色,她才模糊看清,面前的人不是秦寿是谁。
他一身玄色夜行衣,长发整整齐齐的束了起来,一身干练又杀伐的果断。
她心神一松,抬手拍的就挥开他的手,低斥道,“偷鸡摸狗的作甚?”
秦寿顺势在床沿坐下,并探手取来她的外衫,扔她脸上道,“穿上,晚了就捉不到皇后的马脚了。”
闻言,雒妃神色一震,她一翻身爬将起来,三两下穿好外衫,又套上绣鞋,眸子晶亮地站秦寿面前望着她,当真一副期待的模样。
秦寿眉目放柔,他上下瞧了她,又多拿了件暗色的纱衣罩她身上,那纱衣很宽大,一穿上,就能将她全身上下都拢了起来。
这般妥当后,秦寿才一揽她细腰,并不走正门,悄无声息地从窗户跳了出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