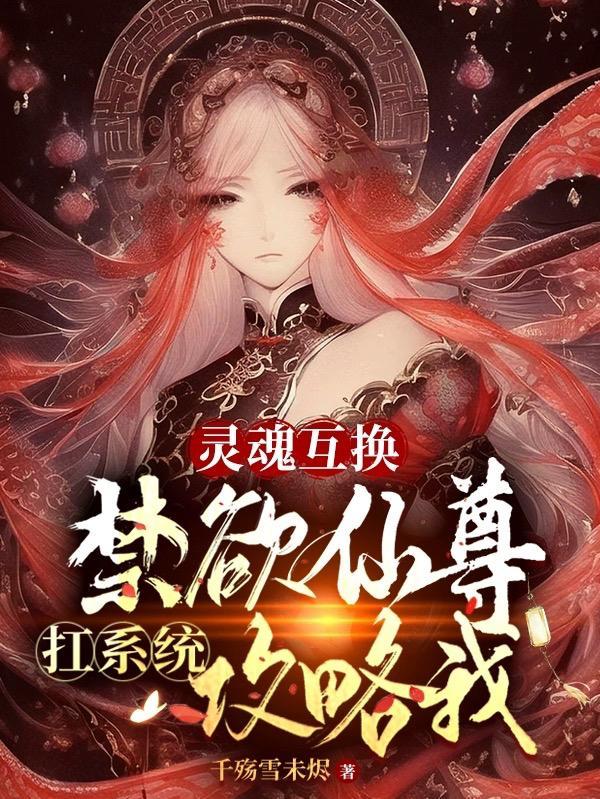乐文小说中文>暗许年年[校园] > 第176章(第1页)
第176章(第1页)
更?不用说同学、同辈人,谁惹他?,他?决计让他?后悔。只是抢个篮球场也要打掉别人两颗门牙这类事,他?没?少干。他?的道德感并不那么充裕,他?的信条就是在能力?范围内让自己舒坦,所以欺负别人只是手?段。
可是这一刻,他?真的体会到怕。
他?望见踡缩在房间角落里的女孩子,殷红的双眼,握着一只半碎的玻璃杯,尖锐的一端正对?着她自己的咽喉,随时?有可能把她细弱的脖颈刺穿。有红色的液体顺着那玻璃一滴一滴地?下来,流到她洁白?的手?臂。
她只穿着一件白?色内衣和小短裤。其它什么都没?有。一件都没?给?她多留。天杀的,就那样踡缩在角落里。
那一刻,祁成全身上下,所有的神经,只剩下一种感觉,就是恐惧。
史无前例地?,觉得人怎么能这么缺德!怎么能忍得下心,把这样一个女孩子弄成这样?
眼神死死盯着那抵在白?皙脖颈上的玻璃尖,他?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怕。
那是一股从骨髓深处蔓延开来的寒意,瞬间遍布全身每一寸领地?,让你失了思维、失了计较、全然不知晓身在何处,想动一下都是徒劳。
屋子里有四个男人,很年轻。都在发呆。
大约先是被那女孩子要插血管的疯狂行为吓傻了,后来突然间房门又被人踹开,这四人直接就懵了,手?不是手?、脚不是脚的。
其中一个看清祁成身后赶来的警察制服的一个衣角,腿上一软就跪了下来。
祁成径直冲向阮念,他?眼睛很难睁开,并看得不甚清楚,房间太小,路上被个人影挡了路,也辨不清谁是谁,一胳膊把那呆立的人形撞到墙上。
其它几个人都愣在原地?,被突然出现的这个人和门口一群警察吓傻了。
他?走近她,轻轻唤她“阮念”,跪在她身旁,试着去拿她手?里的尖玻璃。
她抖得厉害,攥着璃璃的手?却不松开,又往脖了上扎深了些。祁成看得一痛,跟扎在自己脖子上似的,难以遏制的,是一种炸毁世界的冲动。
他?忙撤了力?,只用两根手?指紧紧捏着那玻璃,虚着声音哄她“别怕”,告诉她“是我”“祁成”。直到怀里的女孩子,渐渐回?过神来,扬着脸望着他?。
他?知道她认不出,于是紧紧盯着她,又认真地?说了一遍,“我是祁成。”
她的手?卸了力?,这才把玻璃让他?拿开去。把她整个嵌在自己怀里,全部、整个,生?怕一丝一毫漏在外面。他?只想把她塞进他?身体里。
身后一阵阵嘈杂的厉喝声、撞击声、脚步声、告饶声,他?全然不觉。
阮念死死揪上他?的衣裳,叫了一声“祁成”,然后‘哇’的一下哭了出来,他?这才感觉自己还活着,沉沉地?,落了地?。
之后的很久,祁成一直没?想明白?一个问题。当时?,他?刚进屋那一瞬间,就应该把那几个畜生?杀了的,他?怎么没?想起来?
他?很后悔。不知道为什么就跟傻了似的。原本没?觉得自己是这么窝囊的人。
就只会抱着她,真的没?有任何其它的心思、任何想法。报仇什么的,那一刻他?连想都没?想到。
只是紧紧抱着她、哄她,她哭,搞不好他?也哭了。
陆有川说的,他?随后很快带着保镖和警察过来的时?候,说他?整张脸都是湿的。虽然祁成一再解释说,是在酒店一楼,警察朝他?喷了辣椒水导致的。无奈陆有川死活不相信。
“鼻涕眼泪的,”陆有川绘声绘色地?,两只手?一张摆得很夸张,“而且很白?痴地?跪在地?上。从头到尾只会说两个字,‘不怕’‘不怕’。跟复读机似的。”
陆有川见阮念身上就只剩了一套内衣内裤,白?花花的大腿和胳膊全露在外面,这实在不像样子,赶紧清场,把屋子里的人都往外赶。
回?过头来,找了个毯子想给?阮念盖一下,刚刚凑近,差点被祁成把脑袋揪下来。腥红的眼睛,狠得像要吃人。
他?好心好意千里送毯,最?后得了一个“滚”字。
而后,这人就像突然被打开了某个开关,从复读机的状态一下捋顺了、流畅了,把那女孩子裹吧裹吧交给?陆有川,转身跑了出去。
彼时?那几个男人早被押走了两个,剩下两个走得慢的,也有警察一左一右押着。
祁成跟疯了似的,追到楼梯间,一脚从后面踹去,不知哪来那么大劲,连罪犯带警察全滚下了楼梯。
陆有川真的很想骂娘。
他?又不得不赶紧联系律师,还得帮这疯子摆脱袭警的嫌疑。
住在养和医院的第三天。
阮念终于忍不住了,她说“出院吧。我要上学了。”
其时?她正半躺在病床上,背后是柔软的白?色靠枕。她的手?露在白?色被单的外面,被祁成轻轻握着。
“伤口还没?好。”他?轻声细语地?打着商量,硬朗修长的手?指,摩挲在她的手?心。
她的手?指纤细,白?皙洁净的手?心处,有一条半公分长的割口,是当天她举着那碎玻璃时?扎到的。一开始他?还觉得很庆幸,那些流出来的血不是扎到脖子。可后来发现手?心上的伤口也挺疼的,愈合速度太慢了。
阮念无言以对?。
她第一次见有人因为半厘米的扎伤住院的。她真是怕了他?。
正尴尬,外面传来几下敲门声,站在门口的保镖打开房门,有人推着餐车来送餐。阮念刚合适找到机会,准备起身去卫生?间。不料祁成比她敏捷得多,一下拉住,问她“要什么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