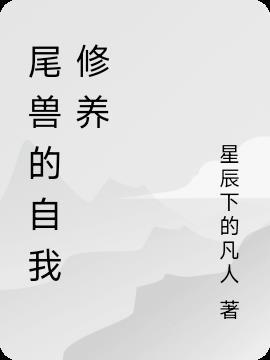乐文小说中文>钓系美人被迫和亲后 > 第165章(第1页)
第165章(第1页)
等屋里全然寂静无声后,斯钦巴日才推门进去,沈怜枝下意识的循声转过头,他看不见,是以大概没发觉自己眉眼间尽是一种化不开的愁绪。
他轻蹙的眉间宛如两把利剑,将斯钦巴日给伤的体无完肤,而斯钦巴日却不得不装傻,他走过去,抬手不动声色地将怜枝的眉间抚平,“怎么不弹下去了?”
怜枝身形一晃,有些心虚——尽管他心里明白斯钦巴日并不清楚《关雎》这首曲子之于他究竟意味着什么,可怜枝的心尖还是不由颤了颤。
沈怜枝侧首,嘴唇轻贴了贴斯钦巴日的手底心,脖颈拉出雪白颀长的一道,是个迷人又讨好的姿态。
“没什么可弹的。”怜枝说。
“很喜欢这首曲子么。”斯钦巴日摸他的脸——人就是这样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,斯钦巴日早已猜出这曲子与陆景策脱不了干系,偏偏还要问,“我记得……你也曾弹予我听过。”
“在草原,你记得么。”斯钦巴图问他。
沈怜枝自然记得,可他却咬着嘴唇不作声,显然是不欲再与斯钦巴日说下去,两个人之间还像隔着一层纱,斯钦巴日重重叹一口气,他有些目光复杂地看着沈怜枝。
斯钦巴日开口叫他:“怜枝。”
“嗯?”
“现在的日子……是你真正想要的么?”
他的声音很轻,问的近乎小心翼翼,沈怜枝忽然很内疚——他不是没看到斯钦巴日的变化……曾经的沈怜枝无论如何都没想到,自己竟有一日会将“小心翼翼”这个词与斯钦巴日相联系在一起。
那个曾经粗暴凶戾的少年,却能在他每一次忧愁与害怕时温柔地揽住他的肩膀轻哄,笨拙却又能使他无比的安心。
斯钦巴日是接受了沈怜枝心里除了他,还有另一个人,可这已是退步了,又退步,退无可退之下的结果,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放在心尖尖上的人,时不时苦这一张脸,思念除他之外的男人——
他不乐意,他可以忍,但是沈怜枝至少也该哄一哄他,让他这颗千疮百孔的心脏好受点。
“当……当然。”怜枝磕磕绊绊的,“现在……有什么不好呢。”
“这样。”斯钦巴日垂眸一笑,“我总怕你觉得闷。”
而后他又有些烦恼地抓了抓头发,“我好像总是无法让你高兴起来……”
在草原的时候是这样,如今也是,他所喜欢的,却非沈怜枝所渴望的,而陆景策与沈怜枝却是表兄弟,尽管斯钦巴日很不愿意承认,但这却是事实——
或许…也许……陆景策比他更懂沈怜枝。
斯钦巴日渴望成为沈怜枝喜欢的样子,他讨厌他粗鲁,那么他便耐下心来,若喜欢他文雅……那他也可以学。
他希望沈怜枝爱他一点,再爱他一点,多爱他,多多地想着他,思念陆景策的时间便会愈来愈短,说不准还会达到最好的结果……沈怜枝终于有一天放下了陆景策,全心全意地爱他。
“你能教我写字么。”斯钦巴日问他。
怜枝一愣,“什么?”
“写字。”斯钦巴日挺挺胸膛,“学写你们大周的字。”
“为什么要学这个?”怜枝疑惑。
斯钦巴日的理由很简单,“陪你写。”
“哄你开心。”
偶尔沈怜枝切实地能体会到斯钦巴日要比他小近两岁,有时斯钦巴日所说的话,能使他的心忽然变得很柔软。
沈怜枝有心逗他,“可我什么都看不见呢,如何教你写?”
而后腰身被斯钦巴日抱住,颈窝处有个毛茸茸的脑袋在不住地蹭,“没关系。”
“那就等你能看见。”斯钦巴日道,他亲亲怜枝的侧脸——
“快点好起来。”
夜晚自然避不了缠绵。
两人依偎在一起时,不由聊起从前的事,怜枝忽然想起斯钦巴日从前着汉服,束发的模样,于是轻轻地笑:“你还是穿胡服时好看。”
“好看有什么用?”斯钦巴日语气幽怨,“你又不喜欢。”
“你笨呀。”怜枝笑,“笨手笨脚的,梳头发梳的四不像。”
斯钦巴日腻着他,“等你能看得见了……你给我梳。”
怜枝便笑着点头。
斯钦巴日坐正了身子,又侧了侧,他无比专注地注视着沈怜枝,目光一动不动,“沈怜枝……”
“你知不知道,你欠我好多事?”
“我会一件一件的,从你身上讨回来的。”
他说的这样郑重,反倒将怜枝逗笑了,怜枝凑过去,挨着他的耳畔,“你怕什么?我还会赖你不成?”
“谁知道啊。“斯钦巴日声音闷闷的,他抱着沈怜枝的腰身,轻闻他身上清浅的香气,他的声音变得逐渐沙哑,“你撒谎成性。”
怜枝没有回话,静谧一隅中,斯钦巴日的呼吸声变得愈来愈沉,落在耳畔的呼吸烫的灼人,沈怜枝有些不自在的动了动,却又被斯钦巴日紧揽回身边,怜枝一手向下,摸到斯钦巴日因为太过用力,手背上凸起的青筋。
于是他知道,斯钦巴日又起了欲。
斯钦巴日对沈怜枝有着无穷无尽的欲望,总是令怜枝难以招架,怜枝有时也弄不清楚他在想什么,斯钦巴日吻他下颌,粗喘着吻,情到浓时,斯钦巴日忽然开口——
“沈怜枝,你再与我成一次亲吧。”
“真真正正的。”斯钦巴日说,“按照你心里想的来,我都听你的……”
怜枝两只手攀着他的脖颈,脸颊潮红,气喘吁吁,“啊……又在说些什么…我们现在,又与成亲的…有什么分别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