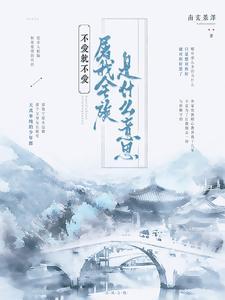乐文小说中文>看见弹幕后,死对头被我钓成翘嘴 > 第185章 他不是阿言他姓秦(第1页)
第185章 他不是阿言他姓秦(第1页)
“我跟你不同,我只要她好!”阿言盯着眼前嫉妒到扭曲的脸,他无动于衷摆弄着手腕上的手表。
是一只表带都褪了色的廉价手表,在网上或者卖表的小铺子里面,最多能卖到五六十都是高价,就这么一只廉价的手表,却是阿言最珍贵的东西,自从戴上这只手表,他除开洗澡就没有取下来过。
贺知安咬着烟:“我是不是还得夸你一句,你真他妈大度!”
他抽的很猛,尼古丁从喉咙侵袭着肺,也没有压下那股无名之火。
姐姐真是让人生气!
为什么就这么不听话呢!
阿言:“别发疯。”
“管好你自已!”贺知安阴郁盯着他这张脸,他忽然笑了,手指捏着烟头,感受着皮肤被灼伤的疼痛,让他享受眯了眯眼睛,“你就不怕我弄死你?”
“那你弄死我好了。”阿言直言不讳。
眼前的贺知安就像是一条毒蛇,缠上你只会越裹越紧,把你勒到窒息,他的毒牙就会穿过你的肌肤,将属于他的毒素注入进你的身体,的确是让人觉得可怕的一个人,阿言倒是不甚在意。
他已经把能安排好的一切都安排好。
就连大小姐……也结婚了呢,他是与贺知安不同的,他可以卑劣利用大小姐的信任,找到回来的借口,在某个大小姐不经意的允许下,靠近她,贪恋去小心翼翼在指尖留下一些大小姐的气息和温度。
这样他就已经满足。
他很清楚,他不会给大小姐带来幸福,井底之蛙只能在井底奢望月光来照拂它,却没有资格从井底爬出来去触碰月亮,他……一直都很清楚,他跟大小姐之间的差距,大小姐很好,这么好的她就该有适合,且与她家世相配的人照顾她余生。
而不是他。
一个从贫困山区靠着资助走出来的穷苦人。
公主不能低头,至少他的大小姐不能为他低头,他舍不得。
贺知安眯着毒蛇一样阴郁的眼睛,他盯着眼前直言不讳的阿言,他眼中没有任何惧怕,是坦然接受死亡的坦然,他是真无所谓!
他是疯子,眼前的阿言是个比他更疯的疯子。
“啧,胆小鬼。”
阿言只是淡淡看着他:“贺知安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?”
贺知安看着眼前破烂的出租屋,不久前,他也住在这样的出租屋,霉臭味混合着下水道泔水的臭味。
“丢了孩子的可云。”
贺知安走了,是被阿言给气走,走时还踹翻了阿言屋里面唯一一把看上去还行的椅子,之所以看上去还行,是他屋里面只有这把椅子,被贺知安给踹翻,本就嘎吱作响的椅子碎开,宛若阿言的人生。
他在破烂的出租屋里面看着碎掉的椅子,他摩挲着手腕上的表,随后吐了口气,去隔壁借来了钉子和锤子,一点一点把碎掉的样子又拼凑好,因为太过于烂,即便用钉子将其再次订好,依旧摇摇晃晃,随时都会再次烂掉。
阿言点着烟,他抬眼看着白色烟雾中的轮廓。
“你来做什么?”